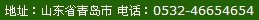|
白癜风初期能治好吗 http://news.39.net/bjzkhbzy/180427/6196834.html 都说:不记得月明楼的,基本都是80后! 将军庙是我童年的乐园。穷人家的孩子,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没上幼儿园,小时候一直在将军庙街头“野蛮生长”,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除了吃饭睡觉,每天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游荡,呼啸成群,衣衫褴褛,我们就象一群无法无天的街头小混混。长大后,看到张乐平先生的漫画《三毛流浪记》,总觉得三毛和他的朋友们身上有我们小时候的影子。 月明楼是将军庙的“地标性建筑”。她在一码头旁边,对面是一个人来人往的菜市场。 那时,我家住在月明楼的正对面,隔街相望。每天出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栋“雄伟”的建筑。确实,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月明楼:大。在我的眼中,月明楼确实太大了,比我那时候看见的任何一栋房子都大,仿佛装得下我整个的童年世界。后来长大后再看见这栋,才发现它其实并不算大,只有两层楼,但很长,大概有三、五十米长。 月明楼楼上一层是如蜂巢一样挤挤挨挨的居民屋(最早是歌厅舞厅),楼下是各种各样的门面房。小时候我看见的月明楼是一栋崭新的砖红色的建筑。那时候根本不用外墙涂料,所有的建筑物都裸露着,呈现红砖本来的颜色。 月明楼茶馆一带是很多小伙伴或者说老益阳人的记忆,小时候父亲带到里面看过皮影戏、喝茶、听书(说书的老人家如今已经去世了,现在他的传承人都70多岁了,在义务教小学生学益阳弹词) 后来我再看到它时,它已经很破败了,在夕阳中佝偻着身体,象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它的身上布满了斑驳的水渍和苔藓,看上去芨芨可危,似乎随时都要倒塌。 再过几年,月明楼就拆掉了,它的原址成了江北大堤的一小段。走在宽阔平坦的大堤上,月明楼的影子再也不到了,只有知道的过来的人都会问这一句:这里就是以前的月明楼吧? 月明楼从人间彻底消失了,没留下任何痕迹,它只存在我们“老人”儿时的记忆里——如果我这个年纪的人也能算“老人”的话! 很可惜,那时候大家很少照相,那时候照相也很贵,只有有钱人家特别日子才照几张,我在网上找了很多年,很难找到月明楼的照片,连介绍都没有了,真给埋没在江北大堤里去了吗? 不知道谁保留了月明楼的照片,或者在月明楼合过影,能把相片翻拍出来给我看看,给我们这代有共同记忆的人看看,我就谢天谢地了。 月明楼的一楼临街,开着形形色色的店铺。这些店铺的经营范围各不相同,但绝不重复,吃穿用一应俱全。它们和散布在将军庙周围的其它店铺一道,形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集市,使将军庙成了益阳市区一个繁华所在,也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月明楼临街的店铺中间,除了最有名也最显眼的月明楼饭店以外,还有几间有趣的店面,充满了我的回忆。。 其中有一个门面是银行。解放后直到80年代初,全国都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其他的银行都是人民银行总行的下属。 不过,月明楼这家银行是下属的下属,准确地说它还算不上是银行,它是中国人民银行益阳市支行在将军庙开设的一个储蓄代办点。那时候的治安非常好,路不拾遗,最坏的人也只会在公共汽车上扒个钱包什么的,给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去抢银行,所以这间储蓄所的戒备一点也不森严,常年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安静地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看书写字。 加上那时候的人们都清贫,父母每月的工资小心着花,也只能勉强保证一家人的温饱,根本没有余钱储蓄。我父母是双职工,家里也只有我们姐弟三个,生活尚且如此,那些收入少、人口多的人家,日子过得还不如我家。所以那时的人很少有进银行存款的,储蓄所的生意十分清淡,平时很少有大人进去,反而是我们小孩常去玩。以至于我后来知道“门可罗雀”这个成语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家储蓄所。要是搁在现在,这样的储蓄所早就关门大吉了,不过,在那个年代,一切为了政治,经济效益是次要的——月明楼这么一栋伟大的建筑,是“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成果,需要有银行来增光! 不过现在想想,还真不能用“门可罗雀”来形容这间储蓄所,因为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小孩进去玩。储蓄所是孩子们最喜欢光顾的场所之一,虽然从来没去办理过业务,但我们几乎天天要去报到。因为储蓄所里靠墙放着一条长椅子,在别的地方玩累了,我们就到椅子上去休息,或坐或躺,舒适随意,宾至如归,一边打量着墙上花花绿绿的宣传画。其中有一张画是我们的最爱,每次看见都要仔细观察一番:上面画着一块钱纸币,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女拖拉机手。这幅画对我们极具震撼力,第一次看见时每个人都激动得几乎晕倒,因为对我们来说,一块钱是一笔不可想象的巨款,平时大家打交道最多的是一分两分的硬币,连五分的都见到少,整张一块的,只在爸爸妈妈口袋里见过,再就是在这张宣传画上。每次大家都要争论一番,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这一块钱究竟能不能用?无数次声嘶力竭、脸红脖子粗之后,总算达成了共识:这钱是能用的,不过要非常小心地剪下来,稍微剪偏一点,人家就不收了。 现在想起觉得好笑,为了防止非分之想,设计宣传画的时候,这张钱本来就印得比真钱大了一截,怎么能用?另外,更主要的是,这张钱只印了女拖拉机手这一面,另一面就是一张白纸,谁会收下只有一面的钱?不过孩子们的世界都很简单,他们永远只会考虑事情的一面。所以几十年来我一直对这一块钱念念不忘。 储蓄所的旁边就是邮电局。那时候邮政和电信是一家,他们在一个锅里舀饭吃,也在同一个门面上班。上世纪70年代,不要说没有私人电话,就是有公用电话的单位也不多,人们要和外地的亲友联系,主要是靠写信或者来邮电局打长途。因为大多数的人家都要寄信打长途,所以邮电局比银行热闹多了,每天进进出出办事的人很多。因为顾客多,邮电局里的工作人员也多,有三四个五大三粗的男人,都神气活现地戴着绿色大盖帽,看见小孩进去就大声呵斥,赶我们出来。邮电局里本来就没什么好玩的,他们不让进去,我们就不进去,讲志气。 邮电局门外墙上挂着一只绿色的邮箱,小孩够不着,大人们要寄信的话,要投到里面。 卫生院有一个“四类份子”,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头。也许是长期挨斗的原因,老人经常是点头哈腰、低眉顺眼的,有什么杂活,谁都可以吩咐他去做,他也从不说多话,总是小跑着完成任务。他在卫生院的地位是如此之低下,以至于我们小孩都能把他支使得团团转,还象大人一样叫他的外号:刘胡子——虽然他的年纪比我爷爷还大,更有一手治疗疔毒的绝技。 有一天,卫生院一个人吩咐他去邮电局发一封信,还派我们几个小孩跟着他,说“怕阶级敌人搞破坏”,实际上是怕他出错。“刘胡子”果然出错了,首先是忘记贴邮票,光着信封就要往邮箱里投。小孩子眼尖嘴快,尖着嗓子“命令”他到柜台上买了邮票贴上了,他又只把信封往邮箱里塞了一半,留下一半露在外面,扭头就要走。我们赶紧提醒他错了,要把信封全部塞进去。“刘胡子”停下来看看我们,又回头看看露出半截的信封,迟疑着说:没错吧?全部塞进去的话,邮电局的人怎么取得出…… 邮电所旁边的一个门面是药店。走进店堂,就是一排很大的玻璃柜台,里面摆满了花花绿绿的药盒,柜台后常年站着一个瘦削的高个子男人,表情严肃。 回忆往事,强哥说他记得“医院里卖船娘子(蝉)壳壳”。知道他说的是小时候卖蝉蜕的事。蝉蜕是一味中药,小时候是有小孩用它卖钱。医院,医院不会直接收购药材,收购是药店的事——医院长大的。 强哥可能是把“船娘子壳壳”卖给了这家药店。 药店收购的不光是蝉蜕,也收购蛇蜕——蛇长大了褪下的皮,还收购尺把长的蜈蚣制成的干。小孩胆小,不敢往拿这些吓人的东西去药店卖,我们最多敢卖个鸡菌子什么的。鸡菌子是鸡的食囊里的那一层壳,除了可以卖给废品店,也可以卖给药店。作为中药,鸡菌子叫鸡内金,焙干后研成粉末服下,专治小儿消化不良——吃哪里补哪里,中医的理论真的很神奇。 那时一年到头也难得吃一次鸡,所以卖鸡菌子是很稀罕的事,卖得最多的是桔子皮。每次吃桔子,妈妈都嘱咐我们要把桔子皮收集起来,晒干之后卖给药店,大概能卖一毛钱一斤。桔核也能卖钱,价格和桔子皮差不多。不过桔子身上最值钱的是桔络,就是桔子肉身上的白须子,听说桔络的价格是桔皮的十倍,也就是一块钱一斤。不过桔络太难得了,一个桔子身上只有几根,晒干后轻如鸿毛,还要费神小心翼翼地剥。 我怀疑我吃一辈子的桔子,可能也收集不到一斤桔络,因此作罢了。不过自家吃的桔子,数量毕竟有限,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捡外面的桔子皮。 有一天晚上外出,归来的路上,一路都有别人扔下的桔子皮;我大喜,不停地弯腰去捡,一会儿就捡了一大捧,那种丰收的喜悦,至今不忘。童年养成的习惯,长大了也改不了。现在我吃桔子,皮依然舍不得扔掉,总是下意识地把它们收集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攒下了一大堆桔子皮,我才开始发愁:这么多桔子皮怎么办?往哪里卖?不要钱白送也行!想想白送都没人要,只好把它们当垃圾扔掉了,兀自心痛! 药店不光是小孩赚钱的地方,也是我们花钱的地方。手上有几个钱的时候,我们会凑上五分钱,到药店去买一瓶桂子油,拿回家找一张白纸,把桂油仔细地往纸上涂匀,晾干后放到口袋里,一边玩,一边撕下一小块,放在口里细细地吮,把纸上的桂油吮完了,才恋恋不舍地吐出残纸。这种桂油纸除了辣味再没有别的味道了,可我们照样吮得津津有味,一张纸能吃上一天。桂油纸,这竟然也是我们童年的零食之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 月明楼里还有一家白铁店,大块的白铁皮裁剪之后,敲敲打打一番,就做成了一人多高的油桶。偶尔也做巨大的酒罐,有半间房子大,也有半层楼那么高,焊着同样巨大的铁架子和铁楼梯。一个酒罐做成后没有卖掉,摆在路边成了小孩的玩具。我们高兴地在罐子上爬上爬下、嬉戏玩闹,那种兴奋和现在的孩子玩充气城堡差不多,只是安全性不可同日而语。后来想起我都后怕,当时万一哪个小孩出了事,那责任应该算谁的?好在从来没出过事。 不过我对白铁店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持续不断的敲击声。那声音空洞、悠扬,伴我度过了多少个昏昏欲睡的午后。我与街头野孩子不同的是是,吃过午饭后不能马上出去玩,而是要午睡。刚开始我不愿意,质问妈妈为什么别人可以在外面玩,只有我一个人要午睡?妈妈不给我解释为什么,只是骂着我上了竹床。我不敢反抗,躺在床上听着外面同伴们嬉闹的声音,满腔悲愤,委屈得要哭了,暗暗发誓一定不能睡着,来报复妈妈的强迫政策。 可耳畔不断传来木锤敲打铁皮的声音,缓慢而悠远,节奏一直没有变化,就那么不紧不慢“咣,咣,咣……”悠悠地响着。听着这个声音,不一会儿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直睡到太阳偏西、妈妈去上下午班了才起来。 月明楼还一个门面是蚊烟厂,厂里做的白色纸蚊烟有一两尺长,点的时候,象白花蛇一样盘踞在铁盖上,驱蚊效果特别好。蚊烟厂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草药呛人的味道和锯木灰的清香,那是老城的味道,也是我们童年的气息。 夜幕降临,月明楼的一个门面房里灯火通明,大瓦数的电灯泡高高挂起。里面几十个光头老头子聚集一堂,聚精会神地听一个瞎子说书。瞎子用本地话说一通,就操起手中的乐器“铿铿铿“弹一阵,声音激越。我们不认识那种乐器,就仿照声音叫它“嘭迪嘭”;长大后,对照书本上的图片我认出了,它是月琴。孩子们对说书没有兴趣,却很喜欢这种热闹的气氛,却不能进去陪老头们坐着,坐在里面要两角钱,我们出不起,就聚集在外面边玩边听,一直到瞎子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才一哄而散。 不过,我是听不到散场的。天刚黑过,妈妈就把我抓回去了,不管我怎么哀求都没用。 天黑后不准再在外面玩,这也是我和朋友们不同的地方。 微益阳:现全市寻找益阳当年月明楼的故事、相片和所有点滴记忆。也寻找那个时代的伙伴们,请看到的此文的微友帮我们传播下此文,60、70年代的我们谢谢你啦! 点击下面个文章,分别收看往昔回忆,记得发给更多儿时伙伴看哟。 寻找将军庙的儿时伙伴 瞎子挑水——70年代老城人的集体回忆! 将军庙——请给老益阳人看看..... 请
|
当前位置: 益阳市 >这栋楼,知不知道,一下就暴露出你的年龄
时间:2021/8/1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总期官宣益阳市赫山区万源学校
- 下一篇文章: 试吃品鉴第十一期鲜味馆带你六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