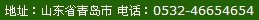|
中科白癜风公益活动 http://www.yushiels.com/npxbb/npxlf/ 04:26 兀·咯·囡 兀,是一个会意字。《说文》:“兀,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以“人”上面加“一”来表示高而上平的概念。今犹有突兀、兀立等词。在口语中,它很早就被借来当指示代词,以“兀的”“兀那”等表示那个、那里、那边等意思。 元·马致远《汉宫秋》:“兀那弹琵琶的是那位娘娘?”《水浒传》第十四回:“兀那都头不要走!”《二刻拍案惊奇·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一人指道:‘兀的不是王秀才来也!’” 益阳方言里也用“兀”,只是它不读wù,而是读ò。益阳人讲“那里”为“兀里”,“那边”为“兀边”,“那个人”为“兀只(个)人”,“哪里”为“兀(或何)海(嗨)”,等等。 从上面所引例子,可以看出,今天普通话的“那”,是由古代口语词“兀那”中保留下“那”,而益阳话是由“兀那”中保留下了“兀”。在南方方言里,保留下“兀”的还有很多,在吴、闽、客、赣语里都找得到例子。只是读音有异,不认真探讨,不知道就是“兀”字。 咯是多音字,益阳人常读两个音:gó、lò。前者相当于普通话的“这”。方言说“这里”为“咯里”,“这是”为“咯是”,“这个”为“咯只”。“咯”读lò时,当语气助词,用得很广。读者可自己体会。 安化人讲话的特征被人概括为“咯些些兀些些,或若或若囝把戏”。 “咯些些”就是“这些”,“兀些些”就是“那些”。“或”古汉语是“有人”“有的”,“若”为“可能、假如、如果”,那么“或若”是“有可能”“有某种可能”,再引申为“随便”“随意”。 安化人“些”用得多,有部分是语气助词,属于古楚语的遗存。《楚辞·招魂》里有:“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这种用法的“些”不见于《诗经》,乃楚语特有。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今夔峡湖湘南北僚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可为一佐证。而《楚辞》中用得更多的“兮”,今普通话读为xī,其实这个字在《楚辞》里本来的读音接近“啊”。 再讲“囝把戏”。 囡、囝,都是后来造的字,《说文》里没有。普通话都读nān,义为小孩,多用于记录吴越方言。新中国成立之后,将两个字规范为一个——囡。而“囝”保留另一个读音jiǎn,义为儿子、儿女。囡与囝,都是会意字,女或子在家的保护下,表示孩子还小,还不能单独外出。 益阳人称孩子为小伢几、小妹几、小鬼、小将、小把戏等。而安化、桃江人多称小孩为“niàng伢几”“niàng把戏”。niàng的读音与nān同源,只是演变得不同了。如果写成文章,写成“囡”或“囝”都可以。 安化、桃江人将囡、囝还活用为形容词,当“小”用。既说“囡把戏”“囡伢几”,也说“大的”“囝的”“菜点得太多,桌子太囝哒”“你给我选一块大点的,咯一块太囝哒”等。 “囡”字益阳话也并非不用。有一词叫“囡(nān)苗”,意为瘦弱、瘦小。既可以讲木枋子囡苗,也可以讲某人(尤其是青少年)长得囡苗。“囡苗”之外还有“花苗”,除了细小,更强调有花样,好看。 益阳人讲东西少,是“一点几”“点毛几”,也讲成“囡毛几”。小孩非常小,讲成“囡毛伢几”。 (感谢唐宋轩宋喜梅女士对本期视频场地、字幕的支持) 主讲人简介: 谢国芳,益阳沅江人,益阳日报社高级编辑、益阳市首届优秀社科专家,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其方言研究专著《益阳方言寻根说字》为益阳市社科重点项目,获益阳市社科成果特等奖、湖南省优秀科普作品奖。 (如果您有方言想求解、不同理解想探讨,欢迎识别
|
当前位置: 益阳市 >益方之言益阳话咯只表示这个,那
时间:2024/12/2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益阳223,多云,1422,北风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