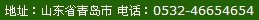|
30多年前在益阳赫山庙读师范,老师中除语言基础知识科目的外大多操各自的方言,益阳话当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方言。汗颜的是,三年时间过去了,普通话还可以算学了个半竹筒水,益阳话我却一句也没学到,而身边羊角、梅城、古楼的同学早是流利的益阳腔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解:为什么操东坪腔的安化人学益阳话那么难?这几年钻进方言学问堆里,总算找到了一些答案。 配图来自网络,图文无关 从广义的范围来说,只要是安化境内长住民众使用的方言都叫安化方言,这就包括边界地使用的纯外境方言比如新化话、溆浦话、宁乡话等。特别是环新化县北境的安化县民众基本操新化话兼通安化话,其中平口镇几乎全境、南金和古楼几乎半境都说新化话。但狭义地看,安化方言不应该包括纯外境方言,而只是县内较宽区域通行的本土方言。 目前较公认的纯县境内方言主要有四种:梅城话、羊角塘话、东坪话、烟溪话。 一个地方的语言,总有比它更大一级的范畴,学术上称归属。安化话是什么归属?得先弄清县内方言的大致分类,弄清这些地区与周边地区古今从属关系,也得稍稍明明白一些声母、韵母、声调、词汇方面的知识。 梅城话。梅城话基本覆盖了传统的前乡片,包括后乡现滔溪镇的大半。清塘铺话、大福话虽然也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但总体上看与梅城话只是略有差别,都可归入梅城话范围。梅城话最大的特点是声母和韵母合并的较多,结果就是音节相对减少。比如:中=登、熊=赢、红=嗯。全国诗词界通行十四新韵“中华诗国开新岁又谱江涛写玉篇”,梅城话里“中”韵的字都归到了“新”韵,梅山诗社的后乡编辑因不明白梅城话规律常常为韵脚问题改得脑壳痛。 安化建县前属益阳县,建县后直属潭州(长沙)府管辖,益阳也同在长沙府管辖范围之内。作为邻地,梅城话毋庸置疑受到益阳话的影响;作为辖地,特别是作为县城,梅城话更会无限主动地向长沙话靠拢。长沙话的部分去声,听上去好像是要说普通话的阳平声,最后却落在了普通话的去声上,方言学上称为阴去;梅城话也是如此。梅城话与长沙话声调最大区别在上声,长沙话的的上声是阳上,听上去好像是要说普通话的去声,最后却落在了上声上;梅城话的上声接近普通话。 羊角塘话。羊角塘话主要通行于现羊角塘镇,原二都地区。羊角塘话最独特的特征是“知”、“刺”类音的汉字全读成翘舌音,“诗”类音却全不翘舌,这在几种安化话中独一无二,放眼全省方言也不多见。羊角塘话的另一显著特征是零声母音节非常多,典型的如:钱=贤=盐,换=汗=碗。 羊角塘虽然在县内地域上与梅城地区隔了小淹镇,但通过桃江又与梅城地区连成了一体。仔细分辨的话,不难听出羊角塘话与梅城话的语音上还是十分亲近的,因为二者都与长沙益阳在地域上相接,都与长沙益阳话是一个体系。这二者的大多去声字如“县”、“外”等,和长沙话益阳话一样,听上去是弱化的普通话上声。但羊角塘话的去声却绝没有梅城话的阴去声调,这也是它与梅城话最大的不同。 东坪话。东坪话包括了江南、冷市、龙塘、田庄、柘溪大部分地区略有差异的方言。马路话、奎溪话,大多介于东坪话与烟溪话之间,自成一类的特征很不明显。小淹话则有一些梅城话、桃江话向东坪话过渡的特点,整体而言还是东坪话范围。这一线北邻常德官话地区,南邻新化邵阳老湘语地区,方言受此二地影响较大,也受西边溆浦地区方言的影响。虽然旧属益阳,但在语上受益阳话的影响不如词汇的影响大。东坪话有一个最显著的语音特点,去声既不像常德官话的高平调,也不像老湘语和梅城话的弱上声,而是弱化的普通话低平声,且大多读去声字都有听上去如普通话去声的入声读音。按阴阳上去声调,东坪话语音无限接近普通话;普通话有的音节在安化话里大多都有,只是张冠李戴的现象十分普遍。 可以说,去声字的读音差别是东坪话与梅城话、羊角塘话乃至益阳话、长沙话最大的差别。所以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方言时,前乡人认为东坪话的去声和阴平声不分,而后乡人则认为前乡人的去声就是上声。羊角塘话与东坪话之间互相影响最大的是用词,名词后加“的”是最大的共同点。如“桌的”、“凳的”、“么的”。 烟溪话。烟溪话相对而言是最难区分的一种方言。烟溪话通行于烟溪全境,及古楼、南金和渠江远离新化的区域。烟溪在地域上与马路、东坪地区相连,声母与韵母组合规律基本是相同的,但其上声与去声却分别是阳上与阴去,与相隔较远的长沙话几乎一样,当然也与西南官话一样,在安化话中是唯一的。我们常说烟溪人说话像唱歌一样,为什么?烟溪话只有四个声调,这两个声调都是有音变的,能不像唱歌吗? 说了地域影响,也说了声调差异,还有必要简单说一下声母和韵母。 烟溪地区及马路和东坪地区都是南与新化相接的地区,烟溪话、东坪话、新化话共有的一个完全不同于梅城话、羊角塘话的显著特点是都有古浊声母,而梅城话和羊角塘话完全没有,长沙话、益阳话也没有。 举几个例字吧:“婆”、“铜”、“凤”、“共”、“强”、“自”,抛开准确的声调,羊角塘话说出来,婆=模、铜=冻、凤=瓮、共=拱、强=羊、自=是;梅城话说出来,婆=波、铜=登、凤=瓮、共=梗、强=将、自=治;用普通话说出来,婆=坡、铜=疼、凤=风、共=供、强=抢、自=渍,但在烟溪话和东坪话里,这些都不是。浊声母发音出来的一个特点是音调高不起来,一般不出现在阴平声和上声中,以阳平声和去声、入声占多。 现在可以大致给安化话划分归属了。益阳话和长沙话,是典型的新湘语长益片方言。梅城话、羊角塘话特征与之十分相近,所以学术界基本将二者归到了新湘语长益片方言,我们不妨看作简化了的新湘语。东坪话是常德官话与老湘语娄邵片之间的过渡方言,是语音官话化倾向强烈的老湘语;普通话里的“f”声母在东坪话里全部读“h”,比如:佛=忽、方=荒,这是老湘语的最本质特点之一。烟溪话虽然在音调上是简化了的长沙话并无限接近西南官话,但因其完全保留老湘语古浊声母,并且与新化话一样保留老湘语、赣语独有词“个(上声)”,如“么个事”、“何地搞个”,与东坪话一起归入老湘语更妥。 弄清了几种安化方言拥有的个性特征,再将它们与周边地方言比较,我终于算是明白为什么总是学不会益阳话了。将浊声母清化、去声上声化、上声先发去声音、韵母大调整,怎么弄得了!当然也明白了为什么操东坪腔的普通话学习进步较快,成为普通话测试员的也较多,原来与东坪话本身的先天因素不无关联。 现代社会,人流交往日益频繁,语言的融合速度超出想象,但就方言看这种融合有时又很搞笑。东坪镇成为县城,自然也成为全县的文化中心,说梅城话的、羊角塘话的也会有意地意地融合进东坪话最典型因子:古浊声母。安化属益阳市管辖,政府和部门官员中来自益阳的多,说梅城话与羊角塘话的官员也不少,操东坪话、烟溪话的还常常会刻意地将古浊声母清化。说东坪话的也不自觉地会融入益阳话的是典型因子:去声上声化,最最说得多的一个字是:县=显。但这种融合也是很有限度的,只是集中在一些高频词中,说的话多了还是本地方言会占上风。而且,融入的个别字听起来总感觉有些生份、不纯正。当然,随着普通话的强势推广,不管操哪种话的都会不由自主地掺杂进普通话语音和词汇要素,求得最多的共同点,在公众场合渐渐地放弃了纯正的本地方言,纯正方言的交流范围日渐萎缩,这也是大势所趋。 方言的特征当然还体现在组词规则特别是特有词、常用词上,体现在声母、韵母、音节的组合规律上,以后还会逐一解说。 作者:王青山配图:图文无关 品味安化综合整理编辑:邓迪波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yiyangzx.com/yysdl/5245.html |
当前位置: 益阳市 >品味安化王青山安化话和它的左邻右舍
时间:2020/7/2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益阳名人谢声溢之十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